真正的争战,不是发生在环境、团体或政权之间,而是首先发生在人自己的心灵里!
《境界》独立出品【口述实录】
杨凯乐/文
我生长在湖南岳阳的一个小县城,从小由外公外婆带着。外公是做绸缎生意的世家出身,外婆父亲当时是长沙官员,实际是地下党员。两老家教讲究,做事细致,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
年龄稍长一点,不苟言笑的父亲接替了我生命中权威男性的角色,他继承了苏北中共部队军人出身的爷爷那种严厉和勤俭,他常对我回忆自己小时候辛辛苦苦拖一天板车,用几分钱买糖吃,被爷爷知道后拿皮带痛打的故事。
从小父母对我的学习并不操心,我读书顺其自然。初三,因为厌恶按成绩排名竞争的学习方式及同学间为此的计较,失去了学习的动力。那时候,父亲所在的国企老厂日益凋敝,家里经济状况越来越不济。

上高中以后,母亲眼睛因视网膜脱离先后动了三次手术。家庭的重担虽然没有直接担在我肩上,但我也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压力。在强烈的内疚下,我从高二下学期重新开始认真读书,很偶然的进入了中国政法大学。
入学的头两年,家族亲友中发生了许多变故:父亲一心扑在事业上却被谣言中伤;怀着无钱治病的遗憾病逝的外婆弥留之际的痛苦;失去工作生活没有着落又遭丈夫背叛的小姑卧轨西去……世界开始向我展露残酷而沉重的一面。
懦弱与野蛮的读书人
大二的我,常缓步走在冷清的昌平大道上,脑海汹涌澎湃,幻想成为领袖振臂一呼,期待道德理想国的来临。
无数漫长午夜似懂非懂的阅读中,波普尔的渐进理念,伯林的消极自由,哈耶克的有限理性,推动我对“自由主义”思想开始了不成系统的学习和思考。
1998年,同学和我在法大创办读书社。我们交换阅读“禁书”,私下讨论各种话题。我们不满意死气沉沉的氛围,不屑看行文靡靡的报纸,不认同“学生是产品”的论调,不随从上讲下抄的教学,不附和时尚讲座的风潮。
我们的共识是:“读书仅仅是一种积累知识的方式,作文不过是一种探求真知的方法,为人和行动才是我们展现真理的活的路径”,这也成为读书社的宗旨。
在当时,这个读书社有着堪称独特的活动方式,一群意气风发的学生乃至年轻教师,聚焦于哲学、政治学和法学的书评、影评、理论介绍、学者访谈和读书讨论,思想火花四溅,影响日渐扩大,令得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为之骄傲和欣然。
那夜,6个读书社成员与一位老师畅谈后,夜已深车已尽无法回家;只好住宿于北京林业大学招待所。因不满附近就餐饭店的欺诈行径,我们一怒冲天,恶胆陡生,摔瓶砸台,狠狠撒野。
之后一干人奔出店门,东躲西藏,仓皇逃窜。逃回学校惊魂初定,想起刚刚的作为不禁冒冷汗:这一帮法大的读书人改不了“痞子”的本色。嘴上“胸怀天下,心系苍生”,面对现实世界我们根本就是外强中干,懦弱野蛮!
创社初始难免的功利心态和对读书社荣誉的追求维护,曾让我与屡次用读书社的稿件却忘记标明供稿来源的其他学生社团创始人发生口角。当时,是朋友的安慰、诤友的批评,才让我勇于道歉。
屡次令自己失望的作为,也让我反思:读书写作的人,若不对自己信奉的价值和向往的秩序有所坚持,若不对违背自己所信奉之价值和破坏自己所珍视之秩序的行为有所抵抗,读书写作又有何用?知识人又如何在心灵深处面对知与行的分裂?法律人又怎样以“明公义、倡法治”的信仰理念来言传身教、身体力行?

100元的权利启蒙
接触到基督信仰之后,我1998年开始到教会聚会,2002年开始在教会中参与一些实际工作。家人与长辈待人处世的方式,塑造了我对人对己严厉、敏感多疑、悲观却又追求完美的性格。
无形中,我将“不苟言笑、严肃冷漠和自尊心极强”的男人形象当作理想。信主之后,我心目中的上帝,也是一个严厉、批评、审判、难有宽恕的神。
这个对上帝有偏差的印象,造成我生命的偏激:待人刻薄,急于因事对人下断语,好批评,性情中缺少慈爱怜悯,结果在教会中以追求神的“公义审判”为名,追求在属灵上“指导”人,其实是“控制”人。
境况顺遂的时候,因着弟兄姊妹给我的爱,性格上的缺点并没有太多暴露,甚至会有更新的可能。
但一旦处于紧张或生命干枯的状态,就习惯于在与人的矛盾冲突中不看别人的道理,或积极分担他的忧虑和压力,反而因着自己接受不了、承受不住,就以消极态度和激烈手段解决问题。
结果常常事与愿违,伤害别人,自己也被紧紧捆绑,不得自由。
那时候,我对神的爱并没信心,因为内心深处的那个“旧我”不相信神的爱是真实的无条件的。所以,我看人对我的爱也是如此没有信心。我的多疑和恐惧也是根源于此。
2002年,在一些法硕同学的推动下,我参与到因学生补助问题与研究生院及校领导面对面的谈判中。前后三次谈判,为将近一半的同级研究生每人争回100元人民币。
事后一位同学遇见我,很困惑地问:“你本科就是法大出来的,明知没啥希望,怎么还跟法硕的掺和在一起?”
“正因为我是法大本科毕业,才知道只能争回那100块钱。” “嗨!100钱有什么意思!”我像当初在谈判桌前一样平静又斩钉截铁的告诉他:“与时间和花费的精力相比,100块钱算不得什么;但作为‘法学神圣殿堂’的学生,我得应当告诉学校什么是公义,我们争的不仅仅是那100块钱,更是自己的权利和人格的尊严!”
法律人如果自己的权利都不去维护,自己的尊严都无法彰显,那么如何为别人维护权利?法律仅仅就是一种赚钱的工具?通晓法律难道只是一种谋生的技能?
我越来越感到,在这个世界,人生将自始至终置于善与恶的争战当中。当时的我认为,善如何胜过恶,在于求善之人如何有着胜过行恶之人的力量和权力;在于求善之人怎样以理性平等地与行恶之人和平地较量。
而我们若不关心政治,不寻求价值,不勇于行动,公力救济力量就会在各种理由下被个人或集团利益所利用掌控。我们对社会的关心少一分,我们价值判断力就偏一寸,我们勇敢的行动差一步,公力救济力量私化的可能性就更大一分,我们权利遭侵犯、尊严被剥夺的现实性就越真切。

异象与幻象,勇气与恐惧
在主持正义的使命情结之下,一种自以为正确的“维权”观点控制了我:维权是基督徒法律人的使命和义务,也就是,每个基督徒法律人都应该投入维权,而不仅仅是特殊的几个人。
我理所当然地由此推理:凡是基督徒法律人的,不知道这个道理的,应该知道;知道这个道理而未参与的,应该参与;应参与而不参与的,就是在躲避责任。
我在教会中开始要求大家若不参与至少是也要理解和支持我的观点。一旦被人不认同或反对,我的严厉批评便随之而来。这种思维方式带给我使命的崇高感和个人的优越感,无形中要求周围人以参与为荣,久而久之,对他们构成一种辖制。
同时,这种自义因为无法与上帝连通,也加深了我的紧张感,使我的生命变得越来越枯干,圣经读得越来越乏味,祷告越来越简短。
三年来,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对一同学习圣经的弟兄姊妹管得太多,我似乎是他们的属灵导师,是他们中的“先知“,结果辖制、压抑甚至伤害了他们,“瞎子领瞎子”,有可能使他们也偏离正道。
最重要也是心理深层最难发现的是:我的恐惧。从一开始从事与维权相关的工作以来,我的紧张和惧怕就从未断过。
这种恐惧,使得我在跟女友交往时常常顾此失彼,言不达意,误会丛生;而且通过我的言行举止,这种恐惧也深深植入与女友的关系里。
直到2009年年初,我终于在极度紧张中心理崩溃,觉得大脑已经不为自己所控制。一位资深的心理医生当时给出的诊断是——濒于精神分裂。
我想只有同样痛苦的人才能够理解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恐惧,整天就像在战场上一样,随时都在跟幻象和思维争斗,筋疲力尽。
我后来从一个忽然意识到的事实中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如此无力:从2008年2月开始,9个月了,我没有打扫过自己的房间一次,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也不能忍受的,但我始终提不起打扫的精力。
恐惧感让我不能处理与每一个人的关系,包括在工作中与老板的关系、在教会与带领人的关系、在查经班与弟兄姊妹的关系、在爱情上与女友的关系。于是我越来越不能忍受老板,开始抱怨教会的状况,对弟兄姊妹也越来越苛责。对女友,我的恐惧使我一方面觉得自己不能给她什么——大房子车子,尽管她并不强求,但甚至可能给不了她一个安定的生活。
我潜意识里想要保护她或者让她有更好的生活而让她离开;另一方面,我的紧张也经常导致对她严苛的批评。种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导致神经绷得紧紧的,时常失态,伤害她。
当我将自己恐惧的事情跟女友分享,带来的一个实际后果是:一方面我在不停攫取她的心力补充自己,另一方面却将自己的垃圾倾倒给我深爱的人。我对女友的依赖,开始从恋人关系变成一种不正常的畸形关系。

她一忍再忍,我却不能看到她生命深处的忧虑与苦痛。
2009年7月份,我慢慢察觉到我心理疾病的根源,发现参与维权政治耗尽我的心力,我的虚荣心被极大的喂养,甚至无暇关心女友,尽管我努力挽回,她却已心冷。
她最后哭着对我的询问,很长一段时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以为你是比较淡泊名利的人,为什么非得要做这种事情?”我当时痛苦地说:“我得做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情!”后来,这种回答成为我反思的起点。
在那段日子,想起过去就如刀扎在胸口。我突然醒悟到,长久以来不是耶稣基督而是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实质上成为了我行事为人的原则,尤其是我所谓“勇敢”品质的来源。
颇具反讽的是,我2006年曾写下“论勇气——兼论基督徒与公民”,将公民与基督徒的勇气作一比较,表面上引用《圣经》分析基督徒与公民所谓同一品质的差异,实质里混杂着希腊政治哲学及启蒙运动的人本观念。
其实,当时若自问是否相信复活、天国和地狱时,我是根本不敢作出肯定回答的。
反思中的绝望反而让我只能依靠耶稣,日复一日的痛苦、仇恨、怨毒、挣扎、祷告、呼喊中,我开始越来越深地与耶稣基督联结。
我跟随维权的浪潮,本意虽然是想服侍,但自己却在这浪潮中渐渐迷失,渐渐骄傲,渐渐霸气,觉得自己似乎不是一个平常人,做的也不是平常事,撑起的牌子乃是能吓死人的“拓展天国”。那时的我又怎能明白这个世界的恶与自己的罪之间看似藕断实是丝连?
我认识到,以“公义审判”为名的控制欲,不仅是人际关系中伤害人辖制人的原因,而且是极权社会专制国家出现的根源。若只有所谓的“公义审判”,人就自以为义,久而久之就会被情欲、血气和私利支配其行为。反思到这,我才幡然明白:真正的争战,不是发生在环境、团体或政权之间,而是首先发生在人自己的心灵里。基督徒以此为异象,以为是在为神成就大事,却可能被撒旦借着俗世国度中的名利试探。我的勇气是来自刻意要显出来的男子气,而不是神真正的呼召和信仰的自然流露。
所以,实际上,对我而言,这种“异象”是幻象。

你为什么不祷告?
我已经知道我该怎么办,过去坚持的自以为是的价值观没有了,我开始努力越来越多地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大使命情结和男人情结,去亲近神、依靠神,寻求抓住神给我的信心,哪怕现在是一点点,也相信神的恩典够我用,会加添我的信心。
但是,在与人建立亲密关系上,我依然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枯竭和绝望。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我很想结婚。在相亲的过程中也认识很多姊妹,但我越来越绝望。
长期以来许多负面情绪积累在心里,我发现自己的脾气实在是太糟糕了。我没有信心去爱一个人,怕亏待别人。同时,也发觉自己所做的事,所走的路,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艰难。我常想,让一个我爱和爱我的人一起走这条路,是不是有必要?有时候甚至想是不是应该独身呢?可是终究觉得没这个恩赐。
当我遇到芦苇姊妹的时候,我不太相信自己能够完全地好起来,不相信自己能够没有理由发脾气。所以,在跟她认识、求爱和预备结婚的过程当中,我对她说:
“我担心我亏待你。你是一个很好的姊妹,我将来走什么样的路,我虽然清楚,但不知道是不是你所想要的。我甚至也不知道,我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得神的喜悦。”
芦苇刚跟我认识时,有时偶遇同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夸奖我,我就对她说:“我很感谢他们对我的欣赏和肯定!但是,这些话,你别太当真!我内心的虚伪,我自己很清楚!你马上就会发现!”
芦苇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同寻常!在她的身上,我真看到有基督的馨香。和她相处时,我发现自己简直不是基督徒。
就如我是一个看过《圣经》、相信《圣经》是真的、但又不那么信靠基督的人,看到另外一个人那么相信耶稣基督、居然凡事都祷告,我才发现所谓“属灵的眼光看透万事”、“凡事交托”、“凡事感恩”,原来是这么回事!
与旧我的征战是漫长的,即便在我们确定关系甚至领结婚证后,我心中无缘无故地会冒出不安全感、甚至是恐惧感、那时便会极其粗鲁地发脾气。我难以描述我的态度,但每次吵,都是我在吵,芦苇姊妹并没有吵。
发生事情的时候,她总是说,你为什么不祷告、去寻求神的帮助?一次又一次后,我开始在恐惧和不安全感发生的过程中,逐渐得着神的力量,去为她着想,去平息那没有来由的愤怒、急躁。
另一方面真地在神面前,完全看清了自己的软弱有限。我也完全明白了芦苇姊妹告诉我的:“你碰到了事情,为什么不祷告?”
我对芦苇说:“你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祷告!”因为祷告在我这样的基督徒看来,好像太虚了,不能带来效益,似乎太浪费时间。
其实骨子里,我还是不相信“看不见”的上帝。从芦苇这里,我得到很大的帮助。我才知道原来《创世纪》里所说的“帮助者”,是这样一个含义!她真是扶持我、帮助我,让我与神有实实在在的关系,实实在在的连接。
因着与她的关系,我相信她能服侍我、帮助我,让我与神更亲近。
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芦苇姊妹有她的软弱,有她的缺点,但我若作为她的丈夫,就要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哪里,学习怎样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方式去爱她。
我知道我的爱很缺乏,但我相信和她在一起,在基督里有,因为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版权声明:《境界》所有文章内容欢迎转载,但请注明出处,来自《境界》,并且不得对原始内容做任何修改,请尊重我们的劳动成果。投稿及奉献支持,请联系jingjietougao@gmail.com。如有进一步合作需求,请给我们留言,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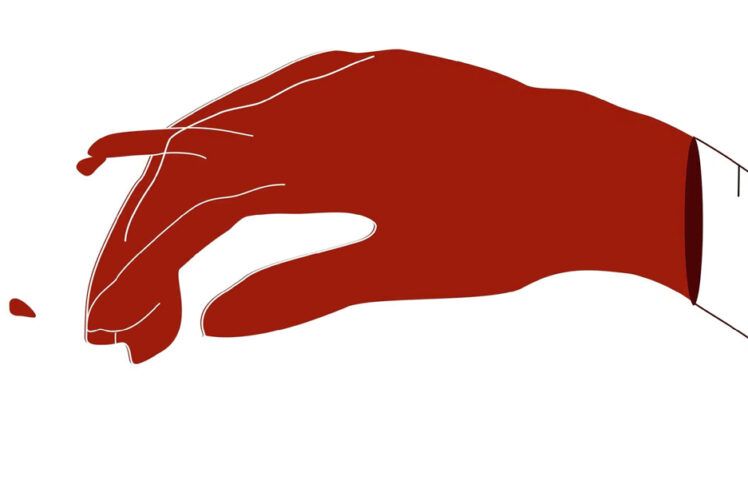


Leave A Reply